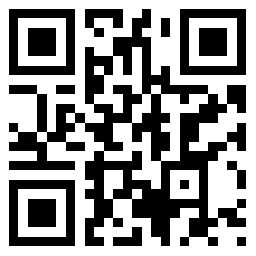
1、沉思與反抗——林賢治評論
阿倫特:沉思與反抗——紀念漢娜·阿倫特誕辰100週年(林賢治)
美國政治學者漢娜·阿倫特的著作,有八種漢譯本,不同的傳記數種。雖然她的主要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在大陸未見出版,但是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她的名字及主要的思想,已爲廣大讀者所知悉。
阿倫特於1906年10月14日生於德國漢諾威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她的父母都是社會民主黨成員,母親還是盧森堡的崇拜者。她在馬堡和弗萊堡大學攻讀哲學、神學和古希臘語,後轉至海德堡大學,先後師從海德格爾和雅斯貝斯,深受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1933年納粹上臺後,參與猶太復國主義的祕密活動,一度被捕,後流寓巴黎。在法國,她繼續爲猶太組織工作。1940年,與流亡的共產主義者海因利希·布呂歇爾結婚。同年,被關進居爾集中營,法國淪陷後,同母親和布呂歇爾一同逃往馬賽,次年前往美國。總的來說,她是喜歡美國的,二戰勝利後,大批德國知識分子返回德國,她堅持留了下來。在這裏,她最先爲猶太文化重建委員會工作,曾任舍肯出版社編輯,芝加哥大學教授,並在多所大學開設講座。其間陸續出版多種政治學著作及其他著作。主要有:《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條件》、《論革命》、《共和危機》、《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黑暗時代的人們》等。1975年12月4日,因發作心肌梗塞,病逝於紐約寓所。
阿倫特的政治學者的形象是在美國完成的。作爲學者,她大大拓寬了政治科學的論域,譬如“極權主義”論,便極具原創性質,它取自時代經驗,爲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政治學經典所未見。由於她堅持自由寫作,因此不能不打破經院式的“學術規範”,她的絕大多數著作,以評論和隨筆的形式出現絕非偶然。然而,在充滿激情的表達中,卻又無處不顯現着她固有的沉思的氣質。她是從哲學走向政治學的。
在實證主義學者看來,阿倫特的著作當有許多不夠嚴謹或者偏頗的地方,事實上,她在生前便遭到不少這樣那樣的損毀。可是關鍵的是,她及時地介入現實,把她的思考集中到帶公共性的問題,“人的處境”問題上面,直逼時代的核心。她確信,真正的思想者不在於完成,而在於打開。不是由自己終結真理,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給人們,而是打開思考之門,讓自己和人們一道在思考中行動,這正是阿倫特作爲一個現代學者不同於傳統學者的地方。

在確立個人身份的時候,阿倫特並不把自己看作是純粹的德國人,或者是純粹的猶太人,而是一個德國的猶太人。她拒絕被德國文化同化,同時拒絕猶太復國主義。對美國來說,她也是“外來的女兒”。她要做一個邊緣人,局外人,“有意識的賤民”。學者總是喜歡標榜“價值中立”,而她爭取的,惟是身份的獨立而已,價值傾向卻是鮮明的。對自由的渴望,使她始終堅持獨立批判的立場,不憚於自我孤立。關於艾希曼審判是最突出的例子。我們看到,她不但從中挑戰廣大社會的慣常的善惡觀念,“美化”屠夫和公敵,而且把矛頭直接指向受害者團體——自己所屬的種族團體——猶太委員會以致全體猶太人,終至於衆叛親離,這需要何等超邁的道德勇氣!她固然不是那類埋首於專業的麻木的學者,但也不是那類與時俱進的聰明的學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學者。她反潮流,反抗她的時代,因爲她確信,她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極端的時代,黑暗的時代。
2、《極權主義》第一次寫極權下的人類境況
極權主義:羣衆運動、組織、宣傳與恐怖
二十世紀人們最爲刻骨銘心的經驗,就是在極權主義統治下的生活。阿倫特於1949年完成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一次系統地描述了這一人類境況,並通過對傳統社會的比較研究,在理論上做了深入的總結。全書共分三部:第一部爲“反猶主義”,第二部爲“帝國主義”,第三部才說到“極權主義”。前面兩部對歐洲18世紀以降的歷史進行多個方面的考察,指出極權主義的崛起,乃是人類文明的一次大崩潰過程,實際上是全書的一個前奏。所以,雅斯貝斯建議從第三部讀起。最後一部對極權主義的起因和條件,表現形態和特點,做了縝密的分析,指出這是“我們時代的重荷”,並且警告說,極權主義並未終結於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終結。
“極權主義”一詞並非阿倫特的發明,而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歐美慣於使用的,但是,阿倫特在著作中賦予它以確定的限界和內涵。極權主義運動是一種大衆運動。“羣衆”、“運動”是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理論中的兩個重要概念。她在書中對“羣衆”和“暴民”做了區分。暴民是從十九世紀階級社會中脫離出來的人們,而羣衆則是階級社會解體的產物,因此不像暴民那樣擁有“階級的基礎”,他們反映的是 “全體人民”的利益,實際上是一羣原子化的人們。極權主義運動,實質上是由這些互相孤立的個人構成的羣衆組織,它的一個最顯著的外部特徵是個體成員必須完全地、無限地、無條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誠。忠誠,是極權統治的心理基礎。極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和精英人物必須不斷維繫羣衆的忠誠,以激發他們在運動中的獻身精神。他們要讓羣衆知道,他們之所以存在於這個世界並佔有一席之地,完全因爲他們屬於一個運動,是政黨中的一個成員,他們只能“受惠於自己所加入的黨和黨交給自己的任務”。運動,不斷地運動,它在實踐上的目標,就是要儘可能地把更多的人們引入其中並組織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維持下去。

在論及極權主義運動時,阿倫特着重指出宣傳和組織二者的作用。極權主義宣傳之所以需要在大衆中反覆不斷地進行,是因爲它的意識形態內容原本便是虛構的,非事實、非經驗的;但是無庸置疑的是,某些觀念通過邏輯推理,能夠產生長期不變性,也可稱爲“徹底性”。阿倫特認爲羣衆由於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間,已然喪失由常識所提供的現實感,極權主義宣傳正好利用邏輯演繹的強制性,以恐怖的力量,爲他們提供現實感的另一種代用品——“科學”的謊言。如果說在極權主義國家裏,宣傳(Propaganda)需要和恐怖相互爲用的話,那麼,在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宣傳便爲灌輸(Indoctrination)所代替了。
關於組織的任務,阿倫特在書中寫道,是“把經過宣傳所粉飾的意識形態虛構的主要內容一一轉化爲現實,並且把各個地方尚未被極權主義化的人們組織起來,使他們按照這種虛構的現實而行動”。這樣的組織是分層級的,有先鋒組織,有精英階層,也有普通成員,領袖則處於核心位置。在這個類似洋蔥頭一般結構的組織內,越靠近運動的中心,越是遠離外部的現實,於是悉數埋入爲極權主義教義所虛擬的世界之中,爲“徹底性”所矇蔽。
1958年,《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第二版,阿倫特加寫了《意識形態與恐怖》一章,取代初版的“結語”部分。她寫道:“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形式的暴政,是一個毫無法紀的管理形式,極力只歸屬於一人。一方面濫用權力,不受法律約束,服從於統治者的利益,敵視被統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懼成爲行動原則,統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統治者——而這些,在我們全部的傳統中都是暴政的標誌。”她在書中對極權主義作爲一種新的國家形式和歷史上各種專制政治、獨裁製和暴政形式做了區分,分析它的“現代性”的特點。在最後一章,她指出,極權國家除了獨一(monolithic)結構,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政黨和國家並存的現象,完全缺乏制度。極權統治蔑視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視自己制訂的法律,發展到全面專政,就是警察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裏,活生生的人被強行塞進恐怖的鐵籠中,從而消滅行爲(活動)的空間——沒有這種空間,就不可能獲得自由的現實狀態。極權統治的結果,人們不但喪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息了在政治領域以致一切領域內的自發性和創造性。整個社會無所作爲。
“極權主義企圖征服和統治全世界,這是一條在一切絕境中最具毀滅性的道路。”對於極權主義對人類的戕害,阿倫特有着切膚之痛,所以傾全力加以揭露,反對“魯莽地一頭鑽進樂觀主義”。可以認爲,《極權主義的起源》不但是她的學術道路的起點,也是她的一生思想中的一個聚合點。後來,她論革命,論共和,論責任倫理等等,都與此密切相關,不妨看作極權主義問題的不同維度的延伸。

平庸的惡
1960年5月1日,在逃的前納粹分子,在猶太人大屠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綁架,隨後帶回以色列。次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在耶路撒冷受審,被判處絞刑。阿倫特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目睹了審判的全過程,根據有關材料,寫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關於平庸的惡魔的報告》在雜誌連續發表,引起軒然大波。
阿倫特的文章被普遍誤解並遭攻擊,主要集中在兩個地方:其一是提出“平庸的惡”的概念,代替此前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出的“極端的惡”的概念,將惡魔艾希曼平庸化;其二是指出猶太人委員會,衆多猶太人領導人對大屠殺同樣負有責任,這無異於拿自己的民族開刀,用阿倫特的話說,她揭開了“整個黑暗的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
在阿倫特的眼中,艾希曼並非惡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國中,他是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一個好黨員,當然沒有理由將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承認,他並非滅絕的組織者,他負責協調並管理將猶太人押往死亡營,只是執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誠履行職責而已。阿倫特寫道:“從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我們的道德準則來看,這種正常比把所有殘酷行爲放在一起還要使我們毛骨悚然。”她認爲艾希曼是“官僚制的殺人者”,因此 同意法庭的判決;但是同時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種獻身於邪惡的罪犯,而是一個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別正邪能力的人。在這裏,她把罪犯與“平庸”聯繫起來,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而且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樣決心‘擺出一種惡人的相道來’。恐怕除了對自己的晉升非常熱心外,沒有其他任何的動機。這種熱心的程度本身也絕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話來表達的話,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麼樣的事情。還因爲他缺少這種想象力。……他並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絕不等同於愚蠢,卻是他成爲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這就是平庸……這種脫離現實與無思想,即可發揮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表現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實,正是我們在耶路撒冷學到的教訓。”
阿倫特強調“平庸的惡可以毀掉整個世界”,實質上是強調思考在政治行動中的意義。這正是她對於極權主義運動的基礎——羣衆問題的深入思考的結果。在極權主義運動中,爲什麼所有的人都跟着像希特勒這樣一個獨裁者跑了?爲什麼一個像納粹主義這樣的專制政體能夠靠像艾希曼這樣粗鄙、膚淺的人來支撐?在阿倫特看來,根本原因就在於整個社會缺乏批判性思考。
還有一個集體不抵抗問題。阿倫特發現,猶太人委員會提供“遣送名單”,從中協助了納粹的滅絕行爲的主題,在審判中被故意迴避了。她指出,猶太人領導人幾乎都無例外地用某種方法,某種理由和納粹合作。沒有他們的積極配合,有計劃的猶太人大屠殺不可能達到後來發生的那種規模。在報告中,阿倫特還列舉了歐洲國家在德國下達驅逐猶太人命令後的不同反應,並做了分析。其中,丹麥、保加利亞、意大利並沒有出現反猶主義;丹麥還公開表示反對意見,幫助隱藏和拯救猶太人,曾經將5919個猶太人運往瑞典。相反,羅馬尼亞公民普遍反猶太人,甚至以自發大屠殺的方式屠戮猶太人,以致黨衛軍爲了貫徹“以一種更爲文明的方式”進行屠殺而不得不進行干預。阿倫特認爲,羅馬尼亞不僅是一個謀殺者的國度,而且是一個墮落的國度。她指出猶太人委員會沒有在“幫助猶太人遷移與幫助納粹驅逐他們”之間做出抉擇,同樣是一種“惡行”。沒有個人的反抗,也沒有集體的反抗——對於納粹在歐洲社會,不僅在德國,對幾乎所有的歐洲各國,不僅在迫害者之間,而且在受害者之間引起的整體性的道德崩潰,她認爲,耶路撒冷審判所提供的內容,是帶衝擊性的。

誰之罪?對於一個民族的空前浩劫的反思,阿倫特在這裏留下的啓示是,必須在法律犯罪與政治、道德上的責任問題作出區分,不但要從政治體制方面追究歷史責任,還要從人性道德方面追究個人和集體的責任。所謂歷史的反思,就是反思責任。正如究詰共同罪責一樣,認爲共同無罪也是不成立的。
關於阿倫特在艾希曼審判中表達的觀點,諾曼·波特萊茲在一篇文章中的概括是準確的:“取代罪大惡極的納粹,她給我們的是“平庸的”納粹;取代作爲高尚純潔的猶太殉教者,她給予我們的是作爲惡的同案犯的猶太人;而代替有罪與無罪的對立的,她給了我們是犯罪者與受害者的‘合作’。”對於一段苦難歷史的批判反思,阿倫特是豐富的,深刻的,但確實是驚世駭俗的。由於她,無情地撕破了一些政治體的卑鄙的僞裝,撕破了人們藉以掩蓋自身的人性弱點的外罩,所以備受攻擊和誹謗也是必然的。
公民參與
1963年,阿倫特的著作《論革命》出版。雅斯貝斯認爲,此書是作者基於在美國的生活經歷的產物,主題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嚴的勇氣;並且評價說,它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極權主義的起源》。阿倫特認爲,革命精神已經失去,她把這看作是現代人的悲劇,從而給予正面的闡釋,把革命與共和聯繫起來,重塑革命精神。從中所體現的作爲一個飽經極權統治迫害的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與不泯的激情,倘若拿來與後文革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告別革命”的論調相比較,確實是很有意思的事。
在書中,阿倫特集中討論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她認爲,兩個革命都極其重視公共自由和大衆福祉,但是美國革命並沒有像法國革命那樣限制公民的個人權利,它的成功經驗表明,革命只能使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她指出,美國這個國家的確有它的特殊性,它所以能夠避免極權主義的影響,就因爲它不具備民族國家那種建基於歷史和文化的統一性意義上的民族一體性,此外,也不曾出現如十九世紀歐洲社會那種具有強大內聚力的階級結構,作爲一個移民國家,原本就是一個大衆社會。但是,美國與歐洲文明是同源的,這也是一個事實。在阿倫特看來,革命和憲法的制訂,在總體上是革命過程中的兩個不同階段,美國革命的一個特點是,它並非一場突發的暴力運動的結果,而是始終依靠衆多參與者普遍的協商和相互契約來發動、推進和維繫的。阿倫特說:“革命的目的在於締造自由。”美國憲法的制訂與定期修正,就是建構和擴大自由空間,將自由制度化。倡導憲政建設,不能只是考慮秩序與程序的確立,而放逐了自由精神與公衆參與;恰恰相反,阿倫特的關於以“評議會制”取代政黨制和代議制,建立一個“參議國家”的近乎政治烏托邦的設想,都是以公衆參與、公共空間的創建爲主要內容的。她認爲,美國憲法體制的本質意義,並不在於保障公民的自由,而在於創建使人民能夠由自己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自由,樹立一種新的權力體系:一、真正體現“權力屬於人民”而非哪一個政黨這一共和原則;二、聯邦憲法體制不是採取主權國家的形式,保證沒有主權的權力存在;三、通過各政治體互相平等,彼此約束,而非定於一尊,實行代替或兼併;四、民族既非政治體的基礎,也就不存在歷史和起源的同質性。在阿倫特看來,美國的開國者們在創建共和政體時,確曾將羅馬的共和政體當作最早的範型,但是,美利堅合衆國的創建並非羅馬的重建,而是新的羅馬的創建,體現了一種延續以政治自由爲第一義的歐洲共和主義傳統的創新精神。

美國在五十年代初曾經一度產生麥卡錫主義,瘋狂迫害共產黨人以及異議知識分子,阿倫特本人也深受其害。但是,這股“劃一主義”的狂流沒有肆虐多久 ,便很快得到糾正。阿倫特深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爲美國擁有以聯邦憲法爲核心的各種自由制度。
《共和危機》是阿倫特於1972年出版的另一本文集,收入三篇論文和一篇訪談錄。這些作品見證了六十年代越南戰爭、學生暴動、黑人民權運動以及七十年代前期以美國爲首的世界性動盪,體現了阿倫特的政治卓識。其中,曾經在《論革命》中所強調的公民參與對於保護美國共和制並促使其健康發展的思想,特別富於時代實踐的意義。
關於政治謊言
1971年6月,《紐約時報》披露了由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授意的機密文件,其中包括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的決策過程的記錄,這就是當時著名的“五角大樓文件事件”。這些文件的內容,暴露了有關政治領域中的欺騙的諸多問題。阿倫特指出,事實是脆弱的,謊言更可能成功,尤其是來自政府的謊言。她說:“由於說謊者擁有預先知曉聽衆希望或者期待聽到些什麼的極大優勢,因此謊言通常比現實更可信,更合乎理性。”其中一些謊言很容易被事實戳穿,但某些類型的謊言則可以將事實真相從人類的存在中完全抹掉,從而侵犯和損害了人類的自由。她指出有兩種相關的說謊方式,一種屬宣傳性質,如越戰;另一種則屬專家、政治智囊人物所爲,它一開始就帶有自我欺騙性質,因爲決策者生活在阿倫特稱之爲“去事實化的世界”。不過,對於政府的欺騙,她並不感到特別沮喪,理由就是她對美國一直處於自由狀態下的新聞機構對民衆服務方面持積極評價的態度,——即使政府文件有着嚴密的保密分級制度,也很難不爲美國民衆所知道。此外,美國人民的天性中具有一種抵制破壞自由的力量的東西,這也是她有信心可以戰勝政府謊言的希望之一。
關於公民不服從
阿倫特相信,公民不服從首先是一個美國現象,因爲它源自一個契約社會中的公民對於法律的道德責任。她將公民不服從與良心的抵制進行區別。公民不服從是集體的、公開的、以挑戰政治權威的正當性爲目的的社會運動,而良心反抗只是個人性行爲。參與公民不服從的人都是有組織的團體的成員,這些團體出於某個觀點的一致性而聯合行動,並共同採取反對政府的立場。當然,這得從憲法上對諸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罷工自由等等基本人權有着切實的保障,就是說,即使同屬於一個基於同意的社會,這種同意也是必須隸屬於不同意的權利的。她提供的思路是一個“契約論傳統”——政府必須取得人民同意(容許異議),如政府已違背託付,人民有權利不服從。儘管公民不服從也許會轉化爲暴力行爲,對於共和制而言具有一定的破壞性,但是,鑑於社會上公民參與的減少,各種形式的自願聯合的減少,阿倫特仍然鼓勵美國政府考慮將公民不服從問題納入法律體系之中,——因爲她相信,這是一個自由國家自信有能力保護人類自由的一種手段。
關於暴力
在《論暴力》一文中,阿倫特對權力、權威、強力和暴力作了區分。她把暴力和權力對立起來,認爲暴力只能導致破壞,但不能創造出權力,一旦開始便無法控制,所以,暴力行動所產生的最可能的結果便是“一個更爲暴力的世界”。而權力,在她看來是尊重人類的多元樣態,使政治自由得到保護的力量。當一個團體或政府發現權力正在喪失時,很容易試圖通過暴力來繼續掌控權力。她認爲這是不可能的,因爲當暴力出現時,權力即明顯地處於危險之中。阿倫特關於暴力的論述,多侷限於一個契約國家—民選政府的理論前提。她將權力過分合理化,不但忽略了權力中隱性的合法性暴力,也忽略了不同政治勢力在某種歷史情勢中的變動關係。這裏,大約是因爲他在68年學生運動中,瞥見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極權主義運動中羣衆的不祥的陰影吧?

等待啓明
阿倫特以一種新異的文體風格,寫作了一本書,名叫《黑暗時代的人們》。所謂黑暗時代,當是她所經歷的二十世紀,主宰這一時期的極權主義和官僚政治;按她的說法,同時帶有象徵的性質,採用的是較廣泛的意義。其中,她寫了從萊辛到同時代人中的多位詩人、作家、哲學家,包括盧森堡這樣的革命者,提供了一個處於精神領域中的人物譜系。當時代將人們捲入屠殺、混亂、飢餓,不義與絕望之中時,作爲“時代的代表”,這少數人卻幾乎不受它的控制和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作爲時代的沉思者,阿倫特無疑同樣是其中優秀的一員。如果從專業愛好來說,她應當埋首於哲學研究;事實上,直到臨終前,她仍然進行着嚴肅的哲學思考。她的最後一部未竟的著作,就是《精神生活》。她本人聲稱,她的主要活動方式是思考,而不是一個長於行動的人。在瀰漫着鬥爭氣息的日子裏,她沒有成爲一名革命者或是抵抗運動的成員,然而,她的思考卻不能不一再地被現實政治問題——人類生存最急迫的問題——所打斷。這樣的思考不同於一般學者的思考在於,它並非服務於知識的目的,而是與實際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密切相關,是對於生存意義的探尋。阿倫特試圖通過思考打破現實——主要來自體制——的遮蔽,阻止人類作僞和行惡,敞開廣大的公共空間,這樣的思考,不能不帶上批判與反抗的性質。在《人的條件》中,她承認:“事實上,在專制條件下行動比思想來得容易。”爲了人類的自由生存,她爲自己選擇了最孤立、最需要堅忍、最艱難的工作:思考。
在《黑暗時代的人們》的序言末尾,阿倫特如此表達她的信念:“即使是在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啓明(illumination),這種啓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着,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阿倫特愛這個世界,她和她的著作,就是這樣一種充滿溫暖的光輝,使我們在黑暗中感知人性和真理的存在而深受鼓舞。
 曹操手下的文武將:羣星璀璨司馬懿笑到最後
曹操手下的文武將:羣星璀璨司馬懿笑到最後  陶謙讓徐州與劉備:背後的真相與權力博弈
陶謙讓徐州與劉備:背後的真相與權力博弈  王翦之子——王賁的傳奇人生
王翦之子——王賁的傳奇人生  歷史與傳說:劉安殺妻款待劉備的真實性探討
歷史與傳說:劉安殺妻款待劉備的真實性探討  權力的陰影——解析劉恆登基後的子嗣之殤
權力的陰影——解析劉恆登基後的子嗣之殤  王允智謀與長安的陷落:三國時期的權謀與戰爭
王允智謀與長安的陷落:三國時期的權謀與戰爭  歷史上元朝大臣阿合馬怎麼死的?阿合馬生平簡介
歷史上元朝大臣阿合馬怎麼死的?阿合馬生平簡介  三國智謀傳奇:五位謀士的遺言對比
三國智謀傳奇:五位謀士的遺言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