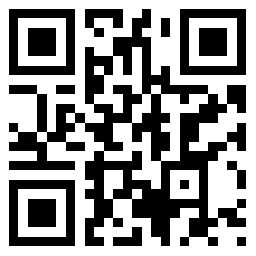
"八旗子弟"是什麼?很多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但是年輕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關以前,17世紀初,努爾哈赤(清太祖)把滿洲軍隊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後來因爲人數一天天增加(以滿人爲主,也包括少量蒙、漢、朝鮮、俄羅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擴充爲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別,是除了原來的正黃、正紅、正白、正藍之外,再加上鑲黃、鑲紅、鑲白、鑲藍。這些旗的編制,是合軍政、民政於一體的。滿洲的貴、賤,軍、民,都編了進去,受旗制的約束。後來,隨着軍事的發展,又增編了“蒙古旗”和“漢軍旗”。三類軍旗各有八旗,實際上共爲二十四旗。原來的本部,由於區別上的需要就專稱“滿洲旗”了。
清兵入關的時候,這些“旗下人”或者說“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騎善射,勇於征戰的。入關以後,他們大抵受到了世代的優待。和皇室血緣親近,地位崇隆的,當了王公大臣,什麼親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之類;地位小的,當什麼參領、佐領;最小最小的,也當一名旗兵。由於他們參與“開國”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祿或者受到照顧。特別是滿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們大抵是滿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隨清宗室到處征戰的漢人,即歸附已久的“舊人”置身其間。清代的制度,規定他們不準隨便離開本旗,在京的也不準隨便離京。憑祖宗的福廕,他們好些人世代有個官銜,領月錢過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當兵,領一份錢糧。但是家族繁衍,人越來越多。有的人名義上還是參領佐領,但實際上已經並不帶兵,有的人名義還是驍騎校,但是已經不會騎馬。更甚的,由於子孫大量繁殖的結果,每家每戶的“月錢”不可能累進,“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額有限,也不可能隨便入營。加上上層人物的貪污腐化,大吃空額,能夠入營的旗兵相對來說就更加有限了。這樣,世代遞嬗,不少“旗下人”就窮困下來。他們之中某些有識之士,也覺得長年累月遊手好閒,不事生產,坐吃山空不是辦法,也有去學習手藝的。但是這樣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認爲他們沒有出息。所以就其壓倒的多數而論,“旗下人”大抵是遊手好閒的。
先代的“光榮”,祖輩的“福廕”,特殊的身份,閒逸的生活(靠領月錢過日子),使得許多“旗下人”都非常會享樂,十分怕勞動。男的打茶圍,蓄畫眉,玩票〔玩票〕指非職業演員從事戲曲表演。,賭博,鬥蟋蟀,放風箏,玩樂器,坐茶館,一天到晚盡有大量吃喝玩樂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閒混過日的法門。到了家道日漸中落,越來越入不敷出的時候,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機靈的口舌,就幹上巧取豪奪,誆誆騙騙的事兒了。他們大抵愛賒買東西,明明口袋裏有錢,偏要賒,已經寅吃卯糧了,還是要賒。當時好些人對他們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廣州曾經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區還留下“八旗二馬路”這麼一個名稱。這裏流傳着一個故事:早年有個“旗下人”到茶館喝茶,當堂倌取來沖茶用的蓋盅,還沒有沖水的時候,他就把一隻小鳥放在盅裏,加上蓋子。當堂倌揭開蓋子的時候,小鳥呼的一聲飛走了。於是這旗人就撕開顏面,纏着堂倌索取賠償,狠狠敲了一筆之後,才揚長而去。直到今天,廣州的茶館裏,服務員爲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飲後自己不揭開蓋子的話,服務員是不會主動來沖水的。傳說這種習慣就和這個故事有關。姑不論這是真是假,直到現在仍有這樣的故事流傳,可見當年“八旗子弟”給人的印象了。

周恩來同志曾經提到的“八旗子弟”,應該說是一個特定名稱,它指的不是清兵入關前後,策馬彎弓,英勇善戰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後,逐漸變成了勞動人民的曾經有過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類拔萃、不同凡響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現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紅旗人。他們“旗下人”的身份絲毫不影響他們在文學上的卓越成就。它指的是清末那些憑藉祖宗福廕,領着“月錢”,遊手好閒,好逸惡勞,沾染惡習,腐化沉淪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爲是滿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樣是原屬漢族而祖先進了滿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對於滿族旗人,對於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爲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紅旗下》那篇自傳體的文章中,曾對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繪聲繪色、入木三分的揭露。這裏我想引他的兩段話,以窺見不少旗人淪落的原因以及他們當時的生活方式:
……按照我們的佐領制度,旗人是沒有什麼自由的,不準隨便離開本旗,隨便出京;儘管可以去學手藝,可是難免受人家的輕視。他應該去當兵,騎馬射箭,保衛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來越多,而騎兵的數目是有定額的。於是,老大老二也許補上缺,吃上糧錢,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賦閒。這樣,一家子若有幾個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來越困難。這種制度曾經掃南蕩北,打下天下;這種制度可也逐漸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還有多少人終身失業。
二百多年積下的歷史塵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麼浮沉在有講究的一汪死水裏。是呀,以大姊的公公來說吧,他爲官如何,和會不會衝鋒陷陣,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親友彷彿一致認爲他應當食王祿,唱快書,和養四隻靛頦兒(注:一種小鳥)。同樣地,大姐丈不僅滿意他的“滿天飛元寶”,而且情願隨時爲一隻鴿子而犧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辦多麼要緊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總看着天空,決不考慮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頭上碰個大包。……他們老爺兒倆都聰明、有能力、細心,但都用在從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與刺激。他們在蛐蛐罐子、鴿哨、幹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對天下大事一無所知。他們的一生像作着個細巧的、明白而有點糊塗的夢。
這類人物去當什麼“參領”“佐領”以至什麼名義上更大的官兒,自然沒有辦法不把事情弄糟。當年帝國主義軍艦開到中國沿海耀武揚威,初次見到那些艨艟〔艨艟(méngchōng)〕也寫作蒙衝,古代戰船。這裏借指軍艦。時,揚言“此妖術也,當以烏雞白狗血破之”的,不就是官階雖然比他們高得多,但無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輩也在伯仲之間的八旗王爺將軍一類的人物嗎!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八旗兵”的顢頇〔顢頇(mānhān)〕糊塗且馬虎。腐敗,也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後來的“八旗兵”已經變得腐朽透頂,在戰場上常常一觸即潰,和清軍初入關時那種秣馬厲兵、能征慣戰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擱起這支老隊伍,另行去編練新軍。而編練新軍,又沒法阻止具有進步思想的青年前來參加,起義新軍終於構成了聲勢浩大的革命軍的洪流之一。
重溫這段歷史,我們可以見到,一個人不是憑真才實學,憑艱苦奮鬥,而是憑血統關係,躺在祖先的福廕之下,享受特權,閒逸度生,是終究非衰頹腐敗下去不可的。這樣的事情,該是順治、康熙所始料不及的吧!早期的八旗將領,可以說過的是相當艱苦的生活。今天如果到瀋陽的故宮參觀,可以看到金鑾殿下的廣場上,兩旁分列着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築,那是八旗主帥進見努爾哈赤,入朝議事時的駐宿之處。那些房屋並不大,大概只相當於現代旅館每天十塊錢的房間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帥”們的生活標準了,較之後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來,也是相去很遠的。
憑血統關係,憑祖宗福廕過驕奢閒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漸腐朽,終至於爛得不成樣子。這種事情,實際上並不獨“八旗子弟”爲然,可以說歷朝歷代,都有無數這樣的事例。這真是“前面烏龜爬泥路,後面烏龜照樣爬”,“前車雖覆,後車不鑑”了。在清代之前,明代原本就已經有了類似的活劇。明初朱元璋分封王子爲各地的王,這些王的兒子,嫡長的就繼承王位,世襲不已。其他的王子王女,也各有封贈。由於人數越來越多,一代代傳下去,封號和食祿就依級遞減,例如“鎮國將軍”之下就是什麼“輔國將軍”,“輔國將軍”之下就是什麼“奉國將軍”,“奉國將軍”之下就是什麼“奉恩將軍”之類。有人統計過,明代開國時的幾十個帝王子弟,到了明末,繁衍出來的人數已經數以萬計,這些人躺在祖先榮譽、血統關係的賬本上,過着寄生蟲式的生活,大抵都成了營營擾擾的庸碌之輩。明朝的覆亡,和這麼一大羣人都直接間接向農民進行各種各樣的需索,使人民負擔越來越重,不勝其苦,也是很有關係的。辛亥革命以後,明清式的世襲王公大臣沒有了。但是許多地主人家,他們的兒女還不是換湯不換藥地過着另一種“世襲”的老爺少爺、奶奶小姐式的生活,在血統關係的賬本上度不勞而獲的日子?而在這樣的生活方式中,誰知道究竟滋生了多少的浪蕩子弟、花花公子、賭徒和鴉片煙鬼?
在這方面,西方的資產階級,卻是不簡單地把大量的財產很快付託給兒女,在給他們以相當的教育之後,就鼓勵他們從事一定的工作來獲取酬報。例如小孩補籬笆、種樹之後纔給予一定的獎勵,成人蔘與某種工作之後才按月領薪,並不給予特殊照顧之類。這是有他們比較深遠的用心的。資產階級至少在這些方面,比較歷史上各個剝削階級,顯得稍有見地一些。
在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裏,照理說,幹部子弟不會也不應該變成“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然而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戶的具體環境、具體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們社會裏,儘管有大量幹部子弟成長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親的功勞簿上,也不依靠先輩遺傳下來的“染色體”過非分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長爲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對兒女千依百順,處處讓他們得到非分享受,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來給他們玩耍;他們幹了壞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縱容,走後門,企圖來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兒女變成了新型的“高衙內”“魯齋郎〔魯齋郎〕關漢卿雜劇《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中的一個“高衙內”式人物。”(按:這都是歷史故事裏著名的白鼻公子)。作爲司令公子的“杭州二熊”,後來一個被槍決,一個被判了無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這樣的事情決不是“絕無僅有”的,而是有那麼一小批,因而也就時有所聞了。某市一位副市長的兒子,某縣一個縣委書記的兒子,因殺人傷人而被處以極刑的事情,已經不是什麼新聞。等而次之,沒有受到極刑,但已鋃鐺入獄,或者路人側目的,那就數量更多了。周恩來同志告誡“莫學‘八旗子弟’”,在我們這個封建習氣還嚴重存在的國家,看來是很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那些特權人物、特權分子是錯估了我們的形勢和現實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斬”,立刻受到“現眼報”了。
其實,不僅要教育孩子不可變成“八旗子弟”,對於某些大人來說(按:請注意這個“些”字的準確性),毋寧說自己就必須警惕自己不要變成“八旗子弟”,因爲人是會變的。一個人從革命者變成了老爺和蛀蟲,在歷史上,在現實中,事例是常見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爲置身於法律之上,吃喝玩樂,逍遙度日,以至於利慾薰心,巧取豪奪,肆意橫行,違法亂紀,因而落得個衆人搖頭、身敗名裂的事,難道就很罕見嗎?不!這也是不時聽到的。
這樣看來,“莫學‘八旗子弟’”的告誡對象,比“幹部子女”還要廣一些吧。
寫到這兒,《哀“八旗子弟”》這篇雜文,是可以結束了。最後,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詩人杜牧的兩句長期應驗在某些人身上的話作爲結語:“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