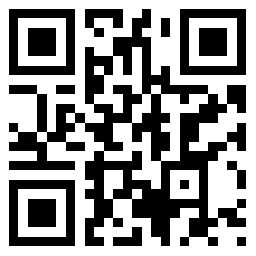
元朝爲什麼短命?中國曆代大一統帝國中最爲短壽?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我們先來說說:爲什麼在統一後百年不到的時間裏大元帝國會積聚成這股能量無比的地火?或言在中國曆代大一統帝國之林中元朝爲什麼這麼短壽?
“地火”的製造——自掘墳墓的元朝統治者讀者朋友可能都知道蒙元帝國,它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疆域最大的大一統帝國,這也是我們中國人常常引以爲傲的一段歷史。但大家可能不太注意這樣的一個事實:元朝立國前後不到百年,這在中國曆代大一統帝國中算得上是短壽的了。那麼元朝的壽命爲什麼這麼短蹙?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軍事大國光環下“黃金家族”子孫們自相殘殺13世紀時,成吉思汗和他的“黃金家族”子孫們猶如颶風一般,以絕對快速戰術席捲歐亞大陸,通過軍事武力手段建立起了東起太平洋、西抵多瑙河、橫跨歐亞大陸的大蒙古國。根據蒙古習俗和傳統規制,“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時節,哥哥弟兄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貴”。成吉思汗曾四次對其子弟、貴戚和勳臣進行了分封,以後逐漸演變成爲欽察汗國、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伊利汗國。
根據成吉思汗遺囑,大蒙古汗之位由第三子窩闊臺繼承,但正式即位行使汗權要經過由宗親、貴戚、勳臣和部族首領組成的忽裏勒臺大會正式確認。忽裏勒臺在蒙元早期歷史上發揮着很重要的作用,除了汗位的繼承外,整個部落的對外戰爭、遷徙和對付天災等重大事件都要經過這種部落“民主大會”的討論。就拿汗位的繼承來說,原任大汗儘管擁有汗位繼承人的提名權,但沒有絕對的決定權,這樣就造成了在忽裏勒臺大會上擁有較強軍事力量的部族軍事領袖有了很大的發言權。一旦遇到意見不合時,勢力強大的軍事首領可能會各自自奉一個大汗,這就造成了成吉思汗後大蒙古汗國事實上的分裂和軍事內戰的不堪局面。
1259年蒙哥大汗在進攻四川合州戰鬥中突然駕崩,擔任漠北留守的蒙哥幼弟阿里不哥開始以監國的身份,行使職權,要求各地的部族首領與貴戚們,包括也在南宋前線作戰的蒙哥另一個弟弟忽必烈趕赴和林參加忽裏勒臺大會,推舉新的蒙古大汗。不料忽必烈在這過程中運動了塔察兒國王,塔察兒領銜諸王沒上和林,1260年他們在開平舉行了忽裏勒臺會議,推舉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這就從事實上破壞了蒙古汗位的繼承傳統,而上臺後的忽必烈又採用了漢人的嫡長子繼承製,汗位與帝位爭奪由此加劇了蒙古“黃金家族”的內部分化與上層貴族之間的矛盾深化,蒙古大汗國土崩瓦解,忽必烈及其子孫所直接掌控的就是中國這部分。1271年忽必烈建國號爲大元,正式即位爲皇帝,按照中國曆代諡號規制方式,忽必烈後被稱爲元世祖。
從形式上來講,雖然元世祖忽必烈奪得了蒙古大汗之位和皇帝之位,雖然從那時起忽裏勒臺還會時不時地召開——那也不過是例行公事、做做花樣文章而已,而從實際角度來看,蒙元歷史進程中的這場變故的潛在影響卻實在不容忽視。元世祖破壞蒙古傳統的忽裏勒臺製度,不僅給四大汗國找到了脫離中央汗國的藉口,使他們紛紛脫離元帝國的統治,而且還爲以後元朝列帝繼承多依賴大臣擁立埋下了禍根,甚至還爲100年後的子孫的不幸種下了苦果——元順帝的孫子脫古思帖木兒就是被阿里不哥的子孫也速迭兒殺死的,死得很慘,當然這是後話了。
事實上從公元1307年成宗死後起,元帝國的權力中心就開始了激烈的皇位爭奪,皇帝像走馬燈似地更換着。從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中,元廷換了8個皇帝,平均3年換1個皇帝,尤其是從1328年到1333年6個年頭中,居然換了6個皇帝,平均每年換1個新皇帝。“黃金家族”的子孫們自相殘殺,政局動盪,皇權日益削弱,而地方勢力卻在肆意擴張,內輕外重,政令不暢,最終演變成軍事混戰的格局,一個強悍的蒙元帝國——絕對的世界一流軍事強國就這樣在轉瞬之間迅速地衰敗下來。
經濟大國耀眼下“黃金家族”子孫們的墮落與軍事大國相匹配,蒙元時代的經濟富有也可堪稱世界一流。據13世紀波斯史學家志費尼記載:以前蒙古人“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這些動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東西”。“他們當中富有的標誌是:他的馬鐙是鐵製的,從而人們可以想象他們的其他奢侈品是什麼樣了。他們過着這種貧窮、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舉,他們才從艱苦轉爲富強,從地獄入天堂,從不毛的沙漠進入歡樂的宮殿,變長期的苦惱爲恬靜的愉快。他們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彼等喜愛之山珍海味,彼等選擇之果品’。飲的是‘麝香所封之’。所以情況成了這種:眼前的世界正是蒙古人的樂園。因爲,西方運來的貨物統統送交給他們,在遙遠的東方包紮起來的物品一律在他們家中拆卸;行囊和錢袋從他們的庫藏中裝得滿滿的。而且他們的日常服飾都鑲以寶石,刺以金鏤;在他們居住地的市場上,寶石和織品如此之賤,以致把它們送回原產地或產礦,它們反倒能以兩倍以上的價格出售,而攜帶織品到他們的居住地,則有似把香菜籽送至起兒漫作禮物,或似把水運到甕蠻作獻納。此外,他們人人都佔有土地,處處都指派有耕夫;他們的糧食,同樣的,豐足富餘,他們的飲料猶如烏滸水般奔流。”
蒙元時代帝國的富庶在《馬可·波羅遊記》中也有所反映:那位舉世聞名的意大利旅行家說東方國家富庶到了黃金鋪滿地的地步。雖然這樣的記載有着很大的誇張成分,但迅速的軍事擴張所帶來的鉅額財富的急劇積聚,那可是不爭的史實。那麼多掠奪來的財富掌握在以“黃金家族”子孫爲首的蒙古貴族手中,在分配製度大有問題的情況下,轉瞬之間成爲肆意揮霍和任意支配的代名詞。譬如,至大四年元仁宗即位後爲報答諸王對他的支持,總共賞賜了金39 550兩,銀1 849 050兩,鈔爲203 279錠,幣帛爲472 488匹。
由於元帝國一直沒有建立相對理性的分配製度,財富支配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賞賜,賞賜有定期賞賜、額外賞賜或言特賜、忽裏勒臺會議後的賞賜以及朝會賞賜等,而每一種賞賜的數額都讓人瞠目結舌。如歲賜元太祖弟哈赤溫大王子濟南王位,“銀一百錠,綿六百二十五斤,小銀色絲五千斤,段三百匹,羊皮一千張”;特賜更是動輒成千上萬兩銀子,如中統四年秋七月癸未日,元世祖忽必烈一次賜“給公主拜忽銀五萬兩,合剌合納銀千兩”。朝會賞賜以元成宗定製爲例,元貞二年十二月“定諸王朝會賜與:太祖位,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世祖位,金各五百兩、銀二萬五千兩;餘各有差”。若再以諸王個案來說事,如“太祖弟斡真那顏位:歲賜,銀一百錠,絹五千九十八匹,綿五千九十八斤,段三百匹,諸物折中統鈔一百二十錠,羊皮五百張,金一十六錠四十五兩。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益都路等處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八千三百一戶,計絲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建寧路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七戶,計鈔二千八百五十五錠”。
一個尚不顯要的斡真那顏位就能得到如此豐厚的收入,那麼遍佈歐亞大陸的“黃金家族”子孫每年都要從元帝國那裏享受到多少的財富?這是一筆從未有人算過但在歷代大一統帝國王朝中絕對算得上是超級財政開支了。
其實自王朝前期起元帝國就開始揹負沉重的經濟包袱。元成宗曾問丞相完澤等:“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回答說:“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元成宗聽後大爲讚賞。“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爲首者,蓋以此。自時厥後,國用浸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於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爲出故也。”
一個國家的財富掌握在一小撮宗親、貴戚、勳臣手裏,即使在所謂的治世尚且還得寅吃卯糧,其最終結果可想而知。國家財政危機日益加劇,帝國政府變本加厲地搜刮百姓,普通人羣日益貧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而與此同時,以“黃金家族”子孫爲核心的宗親、貴戚、勳臣等社會特權階層卻日益腐化與墮落。
元成宗大德年間在元朝歷史上號稱治平之世,可元成宗本人卻是個酒色之徒,當了幾年皇帝了卻連六部長官的賢愚都沒能分清。有一次他跟六部長官說:“你們這幾個人中有人多誤事,可朕不知道他是誰。”到了大德中期以後,這位“治世皇帝”又“連年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壼,外則委之宰臣”。宰臣如伯顏等“固位日久,黨與衆盛,所任之人,徇情弄法,綱紀漸壞”。當年“大德之政,人稱平允,皆後處決”,就是大德年間元朝政治相對安寧全賴皇后卜魯罕居中用事。
至元武宗起情況就愈發糟糕了,武宗是通過政變而登上皇位的,按例他就得對諸王勳舊們大肆濫賞,和林大會之際大加行賞了一次他還嫌不夠,到了上都後又對諸王勳貴們進行了一番濫賞,光給皇太后答己的賞金就有2 700兩,賞銀129 200兩,鈔10 000錠,幣帛22 280匹;賜給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之數亦如之。
“黃金家族”子孫佔有了這麼多錢財要幹什麼?據《元史》記載:元文宗天曆年間,“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五萬匹,綿五千斤”。除了用於揮霍、淫亂外,還有的就是做佛事和供養僧侶。元廷有崇奉藏傳佛教的傳統,每個皇帝在正式即位前都要接受佛戒9次才能榮登大寶,陪同皇帝舉行佛戒儀式的藏傳佛教“國師”“帝師”少則六七人,多則八九人,因爲這些“國師”“帝師”都是“番僧”,語言不通,所以又得用上一批翻譯人員。這些人平時由元廷優渥地奉養着,在皇帝受戒、登基時還得要予以鉅額的賞賜。而元廷中做佛事更是無日不有,最多的時候一年做佛事多達500多次,幾乎要接近每日兩次了。這樣的佛事活動每年要耗費多少財物?元仁宗延祐四年有個這樣的一個統計,要用面439 500斤,油79 000斤,酥油21 870斤,蜜27 300斤。
鉅額財富浪費所帶來的直接後果,除了催化以“黃金家族”子孫爲核心的,由宗親、貴戚、勳臣等組成的社會特權階層的腐化外,還有的就是加劇帝國財政的枯竭,將經濟基礎挖得千瘡百孔。
在經濟基礎被挖空的同時,由於“黃金家族”子孫們推行反動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從而又使得大元帝國的社會統治根基變得愈發脆弱。
蒙古“精英”集團內部小循環削弱了大元帝國立足根基,加深了民族鴻溝說起元朝的民族壓迫,我們可以這麼來形容:愚蠢苦笑,荒誕之至。
元朝把全國的臣民分成四等人:最高等是蒙古人,主要是指漠北各部落的人們,但後來征服的汪古部和乃蠻部卻被劃歸了色目人等;第二等就是色目人,主要是指西夏人、畏兀兒人、回回人、康里人、哈剌魯人、欽察人、阿爾渾人等大西域概念的各族人,甚至還包括髮郎人或拂朗人即歐洲人;第三等是漢人,元朝的漢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漢族人,而是指淮河以北黃河流域、中原地區原金朝統治下的各族人,這也包括了東北地區的契丹人、女真人、高麗人和渤海人等;第四等是南人,也就是最後投降蒙元的南宋臣民,蒙元帝國將南人的地位定得最低。蒙古人賤稱漢人爲“漢子”,賤稱南人爲“蠻子”,充滿了極端的歧視。
這樣的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不僅僅體現在官方主流形態方面,而且還通過法律形式予以固定和強化,如元朝法律規定,如果蒙古人打了漢人,漢人或南人不得還手,只能收集好證據,到由蒙古人壟斷的當地衙門裏去告狀;要是有人違反了,那麼官府要將他“嚴行斷罪”,“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於有司”。漢人與南人殺了蒙古人要被處死,但蒙古人殺漢人、南人則不用償命,只“斷罰出徵,並全徵燒埋銀”;漢人與南人犯有盜竊罪須在臉上刺字,而蒙古人與色目人犯之則免刺字;更有規定漢人和南人不得私有馬匹、不得打獵、不得聚衆百人以上舞槍弄棒、不得搞迎神賽會,不得舉辦划龍舟比賽、不得立市買賣,如有違反就要被處以刑罰,甚至規定禁止江南地區人們夜間點燈,等等。
元朝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反映在政治上,那就是元帝國從中央到地方所有重要的官職都只能由蒙古人來擔任,“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朝中央朝廷以主掌行政事務的中書省、掌握監察大權的御史臺和主管軍事的樞密院爲三大最爲重要機構,其長官中書宰執自元朝建立起直至滅亡,都不曾有一個漢人得以染指。忽必烈時期相對比較開明,但也只有少數漢人擔任過中書省的左右丞或參知政事。大約自此以後,漢人不得參與大元帝國軍政成爲定製。監察系統規定,各道廉訪司即監察官必須首先要選擇蒙古人擔任,或闕,由色目世臣子孫作補充,最後才考慮參以色目人、漢人,而南人就根本沒有在臺省居官任職的可能,也“不宜總兵”,這是忽必烈後的元朝明確規制;地方上的行中書省長官位置也都由蒙古人把持着,只有在官員極爲欠缺的情況下才考慮任用色目人和漢人,南人就更別提了。省以下的路、府、州、縣的官職中漢人只能做總管,最高長官達魯花赤即斷事官必須由蒙古人來擔任。直至基層的社甲,其也限定由北人來充當社主或甲主。對此,元朝文人權衡曾這樣說道:“惜乎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腳。其餘圖大政爲相者,皆根腳人也;居糾彈之首者,又根腳人也;蒞百司之長者,亦根腳人也。而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俱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腳人者,徒能生長富貴,臠羶擁毳,素無學問。內無侍從臺閣之賢,外無論思獻納之彥,是以四海之廣,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皆相率而聽夫臠羶擁毳、飽食暖衣、腥羶之徒,使之坐廊廟,據樞軸,以進天下無籍之徒。嗚呼!是安得而不敗哉?”
元朝的民族歧視也體現在選官制度方面。元朝選官大體有三種:第一種也是最爲主要的一種,那就是怯薛制。怯薛是蒙元宮廷衛隊的意思,由宮廷衛隊出身的人在元朝很吃香,“轉業”後就在政府衙門裏當官,且升遷得很快。所以有人說元朝是武夫當國,我看差不多。
既然怯薛衛隊裏的人這麼吃香,那麼大家都去當兵去了!不行,蒙元政府規定:只有蒙古人、色目人才有權力去當怯薛衛士。這樣一來,漢人與南人只好另謀出路。科舉是漢族士大夫入仕的傳統途徑,也是確保統治階層血液流暢、穩定社會統治基礎的重要手段。可元朝建立後遲遲不開科舉,好不容易熬到元仁宗始開科舉士了,其中也充滿了濃烈的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色彩:蒙古、色目爲一榜,漢人、南人爲另一榜;蒙古人、色目人蔘加科舉考試的人數少,考試題目簡單,但錄用人數卻要比漢人、南人多得多,且授得的官職也要高。第三種選官方式爲學校入仕。“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以國子監爲例,元世祖忽必烈“至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其百人之內,蒙古半之,色目、漢人半之”。到了學校讀書、考試,也是蒙古人、色目人從寬,漢人從嚴;最後出仕,“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漢人從七品”。因此天下士大夫大多鬱郁不得志,對元朝政府懷有極度的冷漠甚至是敵視。
一個國家或政府大行民族歧視或民族壓迫政策,而它的大權卻又一直壟斷在那些所謂的“高貴血統”的子孫手中,搞的是內部小循環;這不僅加大和培植了民族之間的仇恨,而且還造成了其自身的統治基礎越來越脆弱,甚至可以說是自掘墳墓!
大元帝國強控制與全方位腐敗對於統治基礎脆弱的補救辦法,元朝的“黃金家族”子孫們首先想到了祖先起家的好本領——軍事武力強控制。
元朝確立全國統治有一個客觀又“無奈”的前提,那就是以絕對少數的蒙古人控制着人口絕對優勢的漢人與南人。爲了穩定住武力征服之格局,元朝在各地派有鎮戍的駐防軍,駐防軍以蒙古軍和探馬赤軍爲主力,主要駐紮在山東、河洛地區——由此而言,元朝鎮守重點還在中原及其以北地區;又以色目諸部族爲主力組成的探馬赤軍、漢軍和由南宋歸降隊伍組成的新附軍則駐紮在自淮水以南直到南方海南島的廣大地區,由蒙古宗王擔任大將——由少數人來看住多數人,在製造民族矛盾的前提下,或許能起到一時之功效,而就實際而言,相對於北方,淮水以南地區一直是元朝控制的薄弱地帶。
爲了彌補這種駐軍格局帶來的缺陷,元朝政府採取了與駐防軍相結合的社甲制度。社原是中國民間一種自願結合的組織形式,元世祖忽必烈在攻滅南宋之前就開始加以利用,下令給征服地區,規定其50戶人家立爲1社,推選德高望重、知曉農事的老農爲社長,戶數達到100家的,增設一個社長,不足50家的,與鄰近村子合爲一社。設立社長制的目的是要將統治的觸角延伸到社會底層,督促農民勤勉農事,爲大元帝國多生產“愛國糧”,還有就是加強對基層百姓統治。說白了這樣的社長制可謂“以漢治漢”,但元朝統治者又怕漢人“作弊”,所以接下來又命令駐紮在各地的探馬赤軍和蒙古軍隨處入社和編入當地的“社民”。但由於元朝政治上規定蒙古人爲絕對的優等人羣,蒙古人與色目人有隨便居住各地的特權,擁有絕對優越感的蒙古人卻不願與漢人相合爲社。於是在攻滅南宋後,大元帝國改進了方法,在南方地區推行甲主制度。南方人每20家人家爲1甲,由蒙古等北人充任甲主,並賦予其兩大職責:第一,肆意搜刮百姓。據有關史料記載,元朝中葉以後,每年徵收的田稅賦役要比元初增加了20倍。第二,監視南人“異常”與任何反抗,元朝攻滅南宋後規定:“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違者笞二十七,有官者聽贖。其公務急速,及疾病死喪產育之類不禁。諸有司曉鍾未動,寺觀輒鳴鐘者,禁之。諸江南之地,每夜禁鍾以前,市井點燈買賣,曉鍾之後,人家點燈讀書工作者,並不禁。其集衆祠禱者,禁之。諸犯夜拒捕,斮傷徼巡者,杖一百七。”更絕的是元朝統治者還規定了甲主對甲內的平頭百姓擁有絕對的權力:“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盡者又不知凡幾……鼎革後,城鄉遍設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
這就是人們爭議不歇的元代漢族姑娘的初夜權問題,近來網絡上有人對此作了考證,認爲當時蒙古人與漢族人的比例爲1:3333333,其潛臺詞爲一個蒙古男人若要給幾百萬漢族姑娘“破身”,這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忙得過來的“累活”,從而也就否定了蒙古等北人享有漢族姑娘初夜權之說。我們不做無謂的爭論,但筆者自小就在南方長大,老輩們一直堅持講:“我們南方小孩叫父親,不像北方人那樣喊‘爸爸’,而稱‘噠噠’、‘阿噠’,實際上就是講述蒙古人霸佔漢人女孩初夜權的一個客觀反映,‘噠噠’就是‘韃靼’,即漢人對蒙古人的稱呼。”我們更有當今社會的現實註釋:某些地方幹部欺男霸女,不是現代人諷刺其“村村都有丈母孃”麼。“村村都有丈母孃”這話今人誰都懂,不可能每個村都有某些幹部的“丈母孃”,但他們強佔或誘姦女人卻是不爭的史實,而蒙古等北人享有漢族姑娘初夜權也有一樣的道理。連女孩子的初夜權都要獻給北人,一來說明南人地位與人格已經給降到了沒能再低的地步了;二來這樣的性亂加速了元朝社會基層的腐敗與混亂。
伴隨着社會基層的腐敗與混亂,元朝吏治更是腐爛不堪。官場上賣官鬻爵公行,“官以幸求,罪以賄免”,官府賣官居然明目張膽到了明碼標價的地步,就連從事監察的臺憲官“皆諧價而得,往往至數千緡”。由於當時官場幾乎全由蒙古人控制與壟斷,但當道的蒙古人他們大多不諳漢語,不通文墨,只能靠簽署日期、蓋印畫押來處理公事,更有甚者到了“七字鉤不從右七而從左轉,見者爲笑”的程度。因此元朝官場重現了遼、金時代的歷史“奇觀”——“以吏代官”或言“以吏爲官”,它與唐宋時代科舉下所產生的文官有着極大的區別,吏原本就是下級辦事員,用今天話來說就是非正規的科班出身,文化素養差,沒有什麼道德操守,他們利用“職務便利”大搞“創收”,講究的就是“經濟效益最大化”——怎樣從百姓頭上榨取更多的血汗,於是“官冗於上,吏肆於下,言事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正之,勢固然也”。
元末時“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之爲何物”。據元朝文人記載,那時官場上通行敲詐勒索式的八種錢:下屬拜見上官要孝敬“拜見錢”,逢年過節要給“追節錢”,長官過生日要給“生日錢”,討個具體差使做做要給“常例錢”,迎來送往要給“人情錢”,處理公事、斷獄問案事關發送傳票拘票的要給“齎發錢”,打個官司要給“公事錢”,甚至沒什麼事長官的也會向下屬討要“撒花錢”,官吏“創收”多的,行話叫“得手”,出任富有地方爲官的,叫“好地分”,補缺任要職的,叫“好窠窟”。
從上述元朝官場潛規則之隱語看去,不瞭解歷史的人還真以爲是黑社會的“山規”呢!官場已經污濁不堪,大元“公務員”們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外,還有的本領就是喝酒、玩女人。
與元朝官吏們這般腐朽形成極爲鮮明對比的是,廣大底層人民卻掙扎在死亡線上,或言徘徊於地獄門口,一旦遇上天災,更是命懸一線。從泰定元年起,有關天災與饑民、流民記載不絕如縷,如元文宗天曆二年大災荒發生後,陝西饑民就達1 234 000餘人,流民數十萬人,河南饑民達27 400餘人,餓死的有1 950人,發生人相食慘禍的就有51起;江浙、江西、皖南等地饑民60餘萬戶,覈計饑民人數可達300萬人以上;中原地區饑民達676 000餘戶。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爲了穩定人心,元朝統治者命令掌管地方監察的肅正廉訪司官員巡視州縣災情,發放賑濟,蠲免賦稅。可在社會全方位腐敗的情勢下,這些受命巡視的“奉使”們豈會“肅正廉訪”?乘着這個難得的“創收”好機會,他們侵吞賑濟糧款,優哉遊哉地到地方上“瀟灑走一回”。相當程度上主宰地方官仕途命運的“奉使”老爺一來,地方上再窮也要“慷慨大方”地迎來送往,所出的錢財都由小民百姓們來分攤,於是老百姓編了順口溜來諷刺這些“奉使”大老爺:“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
如此肅正廉訪不僅沒能撫卹小民百姓,反而加深了官民矛盾。多少年後親歷元朝官吏貪瀆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曾這樣回憶道:“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善,視之漠然,心實怒之。”
其實當時的朱元璋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小杆子”,而無數個懷有朱元璋一般心態的“大杆子”們早就忍無可忍地起來造反了,尤其是統治相對比較薄弱的江南地區人民的反抗鬥爭自元世祖征服起就一直也沒停止過,“大或數萬,少或千數,在在爲羣”,至元二十年(1283),大小起義有200多處,6年後的至元二十六(1289)迅速增加到了400多處。元朝歷史上所謂的治平之世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到了末世了。至正元年(1341)僅山東的“強盜”多達300餘處,至正七年“盜賊”在元朝首都大都東部的通州蜂擁而起,甚至連大都中心地區也鬧到“強賊四起”的地步。
面對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帝國統治者不斷地調集軍事力量予以鎮壓,可“元朝自平南宋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略不之講”。原本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蒙元軍隊這時“但以飛觴爲飛炮,酒令爲軍令,肉陣爲軍陣,謳歌爲凱歌,兵政於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爲國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於不振也”。





